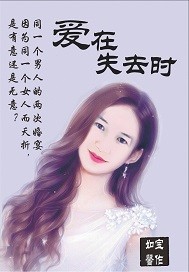最近戏界的第一件大事,就是华东水灾的义演,兰生打算演什么戏虽不清楚,但端端想起当初所拍的全套旦曲,“绵搭絮”、“泣颜回”那几支曲子似乎还萦绕在耳畔,一眼便看中了团凤女蟒、珠子点翠凤冠,又选了两件红缎花帔和云肩,嘱咐永盛戏衣庄制好后送到广德楼给夏老板。
凤冠上的珠子极圆,日光下流转着淡淡的光泽,看到的人都赞手工好,说这几样加一起总得三四百块。红缎花帔下面压了一张纸,上面写着六个字:“冬青旧主敬赠。”
兰生心头一震,他推了她的饭局,她便送行头来,莫非以为他是以退为进、故作矜持么?他微微苦笑,回头对跟包说:“如果继家有人打电话请吃饭,替我答应了。”随后找出一只细藤箱子,把几样东西都放了进去。
果然没多久继六太太的电话便到了,兰生没带跟包,一个人拎着藤箱坐上包月车到了春华楼,进得楼来,依旧是翰墨书香,墨宝满壁。
继六太太事先订好雅间,已和端端先到了,兰生来到门外,就听见两个人的说话声,继六太太用很感叹的口气说:“这人以前虽有臭脾气,对你总算还不错,现在唉……这年月真是人心大变。”
兰生脚下一窒,本来想推门的手复又垂了下去。
里面端端似乎沉吟了一会儿,低声道:“这世上谁能不变呢,我倒觉得没什么。落落者,难合亦难分,这或许倒是他的长处,这人骨子里——六婶你看出来没有,他其实是个挺不快活的人,又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不快活,所以皮簧戏唱得含蓄不露,座上看来花旦俏皮,青衣端庄,未尝不板眼铿锵,吐气扬眉,可是到了昆腔,那种激切悲伤却怎么也藏不住。”
她忽然笑了一声,“听他唱‘又何惜人间再受罚折’,我鼻子酸得差点儿连笛子也吹不下去,总之……都是可怜人。”
兰生只觉一颗心又痛又热,这样的知音话,便是日日相处的宋鉴铭李永胜也未必说得出,或许在某一瞬间,世上有个人比你自己更加懂你。
多么幸运,那个人是她,多么绝望,那个人是她。
一瞬间他只想冲进门去,抱着她大哭,可是任凭心中惊涛骇浪,脚下却半步也挪不动,直到堂倌来换茶水,才咳嗽了一声,挑开门帘走了进去。
端端穿了件淡青直罗旗衫,头发微微蓬松着,一点饰物也无,正慵慵地抚看紫檀桌上的盘龙雕花,听到声响,才将头缓缓抬了起来,她旁边继六太太已含笑向兰生招手,“夏老板,快请坐。”
兰生拎藤箱的手松了又紧,紧了又松,终于打了招呼,坐到她们对面,箱子也放在脚下。他来时本想把行头还给端端立刻就走的,谁知真正见了面,竟又鬼使神差地坐了下来。
继太太太瞅瞅兰生,又看看端端,见一个默坐不语,一个玩赏雕花,暗暗好笑,细忖兰生若真无心,怎么连跟包都不带来,端端若真无意,怎么又替他分辩说好话,可见两人不过假正经,面嫩怕丑,于是和兰生略作寒喧,就借口催菜躲了出去。
兰生见继六太太离开,忍不住抬眼去看端端,谁知端端也正看过来,两人目光一触,那边已格地一笑了出来,端端抿嘴笑说:“看出来没有,六婶要做红娘呢。”
兰生脸上发烧,这话原让人尴尬,她却坦坦然说出口,想来心里霁月光风,可是为什么又要无端撩动他的一池春水?
“你怎么不说话?”她又问:“东西送到了吧,团龙女蟒和点翠凤冠正合‘定情’这折戏穿。”
兰生想起当日并肩拍曲,何等温馨,直到琉璃厂见到徐家桢,才知这份温馨从不属于自己,后来徐家桢出国,她又匆匆嫁了尚云鹏,由始至终,他不过是她生命里的过客。隔墙作别的一夜,早该识清定数。
兰生想到这里,不由硬一硬心肠,淡淡开口,“对不住,林小姐,这几件行头我不能收。”藤箱子提到桌子上打开,露出里面的女蟒珠冠。
端端脸色一僵,勉强笑问:“为什么不能收,尺寸不合适么?”
北京城里有名的戏衣庄都有名角的尺寸,量体裁衣,自非一次,所以尺寸不会不合适,只有送行头的人不合意。
“平白无故,怎么好收您的东西。”
端端微微一笑,“怎么说平白无故,这次义演,继家票房的票友都参加了,我打算唱‘定情’这折,第一次唱大冠生,一定要找个好角儿帮衬,就想到夏老板你了,你不帮我忙,让我再去找谁呢。”
又是这般亲厚语,兰生心里忽悠了一下,虽知道端端常在继家走票,却一直没见过她彩唱,何况是大冠生,女太太们票戏,向来喜欢和名角同台,既可抬高身份,有些许不到处,名角经验多,也能代为弥缝,端端找他配戏,不外也是为了这些,难道为避嫌疑,就把从前的情谊也一笔抹倒?
“你想唱‘定情’一折?”他喃喃低问。
情同谁定?粉墨登场,假凤虚凰,岂不是徒添一回伤心?
端端嗯了一声,抖着女蟒走过来,“你穿给我瞧瞧。”
阳光下的金线灿灿然刺人眼目,兰生陡然一惊,急向后避,强自镇定道:“林小姐,真不巧,我已经答应了辛行长,那天和他配《汾河湾》。”
端端看了他两眼,将女蟒放回箱子,扶着箱子的藤边,缓缓道:“没时间也就算了,并不是非要你和我配戏,我才送你东西。”
兰生的神情更冷,“无功不受禄,林小姐还是收回去吧。”把藤箱又往端端那边推了一推。
藤箱略有些粗糙,这一推过来,端端冷不妨竟被划破了手指,她抽一口气,心里也焦燥起来,挑了挑眉道:“这么说,夏老板以往受禄,必定有功了。那位王太太……”冷笑一声,没有再说下去。
这话含而未申,简直比直说出来更让人难堪。他终于惹火她了,这样也好,利剪剪开蚕丝,不至于越缚越紧,到彼此身败名裂时才来后悔,于是他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,“这就是夏某人自己的事了。”
端端更怒,不住点头道:“好好,原来还是六婶说得对——”忽听吱呀一声,继六太太推门走了进来,她其实并未走远,拦住上菜的堂倌,自己站在门口倾听,直到听见两人吵起来,端端更提到自己,连忙进去打断,目光往桌案上一扫,笑说:“好精致的行头,夏老板,一会儿还要转场么?”
端端赌气往椅子上一坐,“行头是我送的,不过人家不肯收,更不必说义演配戏了。六婶,大概我这辈子不该送人礼,送一回,要讨一回没脸。”
两人不由同时想到初相识时,端端送脂粉绸段到后台的事。
一时堂倌送菜上来,三人便都不说话,待酒菜上齐了,继太太太便绕到端端身后,按住她的肩头,“你可别这么说,让人家夏老板心里怎么过得去,你们可是经过患难的情份,不是忙得脱不开身,绝不会推你。”眼睛饧了兰生一眼,“只是能者多为,夏老板,就是多配一两出,也不妨碍什么吧。来来,坐下来喝杯酒,咱们好好商量商量。”
这话斟情酌理,体谅兰生到十分,又宛宛转转替端端相邀,兰生却只觉得惊心,继六太太想做红娘的话或许不是玩笑,但是尚云鹏却非继六爷可比,端端于自己更没有那份心思,又何必平白授人话柄。
兰生不想再解释,只客客气气道:“您太高看我。实在杂事太多,难任繁巨。”顿了顿又道:“六太太说的不错,我确实还要赶场,先告辞了。”向二人行了个鞠躬礼,转身而出。
继六太太喂了两声,兰生脚步不停,早已去得远了。
端端气得涨红脸,斟满了一杯酒,一饮而尽,耳旁继六太太劝说,你跟这种人动什么真气,他不识抬举,自有识抬举的人。可是不知为什么,端端心里像被棉花塞住一样,堵得难受极了。
继六太太起身出门,回来时见端端还在斟酒,便按住她手,“你等一会儿再喝。”端端却呛得急咳起来,继六太太忙伸手给她拍了拍后背,皱眉道:“知道自己身子弱,还喝这样的急酒。”端端咳个不停,想说话也说不成句,好容易稳下来,抬头和继六太太说:“咱们也走吧。”
继六太太只说再等等,又劝她多吃菜,东拉西扯说些闲事,端端只好听着,又过了一刻钟左右,忽然门帘一挑,走进来一个华服少年,进了门,摘下鼻梁上的茶青色眼镜,但见乌亮的油头,雪白的皮肤,未语先笑,满面春风,竟是继六太太的得意之人小莲芬。
继六太太在端端耳边低声道:“莲芬现在虽没有那姓夏的风头足,也是好多年的红角儿了,难道连出开蒙戏都唱不好?最难得是没有脾气,让他傍着你唱,决不会出什么仳漏。”端端想不到继六太太这样热心荐贤,一时倒怔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