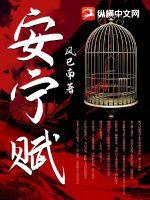端端既怕被人找到,自不会去投奔亲戚,她一个人又全无出门的经验,在火车上一觉醒来,就发现皮箱已被人翻过,衣服虽在,一个装着贵重细软的小包却不翼而飞,万幸身上还有几千块钱,只得在天津找了一家旅馆暂时住下来。
每日关着门整理工尺谱,想起兰生的时候,便去附近茶园听戏,茶园里也偶有北京来的班子,只是端端从前只坐包厢,现在却在散座看戏,穿着又朴素,就像个普普通通女学生的样子,怎会有人注意到她。
旅店中人见她是个单身女客,不免好奇,暗猜她不是逃婚离家的小姐,便是私奔被弃的少奶奶,好在小账不短,也就着意趋奉着。这样浑浑噩噩过了几个月,手中现钱用尽,茶房就不似往常殷勤,到了开饭时候,才慢吞吞端来两个冷馒头。
端端自小娇生惯养,何曾经受过这样困顿的日子,心想自己还会画几笔,不如去书画铺挂挂笔单,胡乱刻了一个“江湖畸零人”的印,想着就算卖不了往日的价钱,一半也是有的。下午向伙计打听了书画店地址,就捡了几张画过去。
不想柜上一听是她画的,看也不看就往外推,端端到第二家留了一个心眼儿,说是一个亲戚画的,江浙画家,在北方虽没什么人知道,但确是米氏嫡派,又说您看这一带青山,隐在烟岚之中,不是很有意境么?
那人呵呵一笑,“小姐,您这就是不懂行了,如今买画的人管什么意境不是意境呢,向来是只认名头儿,要是那名画家画的,哪怕他蘸两个墨圈儿,也有人成百上千花钱来买。要是那不出名的,他就是画只狗能叫,画只鸟能飞,也没人多瞧一眼。别说是米氏嫡派,就算米芾转世,没人认他的东西,也得饿饭。”
端端又是生气,又是凄凉,想自己从前随便画两把扇子,就能卖上百元,那时候还洋洋自得以为是画功出众,真值那个价钱,岂不知画因人重,人家看中的不过是城中名媛、府秘书长掌珠的身份,和画的好坏又有多少关系?到今天穷途落魄,一样的人,一样的画,就变得分文不值了。
回到旅馆,茶房又来催帐,有心给端阳写信,又怕泄露了自己踪迹,无奈只得把身上穿的灰鼠大衣当了,填上了房饭钱。三秋天气,寒风稀稀唆唆钻进脖领子,似乎比冬天还要冷,眼看冬天就快到了,到时又怎样延挨得过去?
屋角墙上挂了一把旧胡琴,不知是哪一位顾曲的客人留下的,端端伸手取了下来,发现琴弦虽有些发涩,倒也能弹,她心里抑郁难消,不免调了调弦,就手弹起来。
胡琴声凄怨悲凉,更激起心中无尽感触,想起这半年来孤身飘泊,旅费用尽,到现在当卖度日,这般有进无出,又能支撑几日?当初在家每月只买衣料和鞋子就得用去几百元,去一次舞厅赏给西崽的小费也有十来块,这二十年来过得是软嫌罗轻,娇嫌帐重的日子,从未受过没钱的苦,哪里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落得这般地步。
心潮翻翻滚滚,只把满腔哀痛都借着琴弦拨出来,忍不住哀哀唱道:“行过东来又转西,举目无亲甚惨凄。衣衫褴褛怎遮体,吹箫讨饭等时机。——英雄落魄谁周济?只落得吹箫讨饭吃。——子胥阀阅门楣第,落魄天涯有谁知!——爹娘啊!”这爹娘两字一出口,只觉千般委屈万般酸痛分沓而来,再也隐忍不住,不由抱着胡琴大哭起来。
窗外风声凄厉,摇撼着树枝不肯稍歇,宿鸟三两只扑剌剌飞起,哀鸣阵阵直逼人心,一霎时更觉意寒魂消,四肢俱软,哽咽得透不过气来。
混沌沌睡去,隔天早晨,管帐却来找她商量,说小姐既然有这样的本领,还愁赚不到钱。东街上有家茶楼叫一壶春,每日都请一些票友清唱,自己和他们掌柜也相识,如果端端愿意消遣,可以替她居中联系,争取丰厚的报酬。
端端低头不语,心知这管帐必是听到了自己唱戏,怕接下来的房饭钱没着落,便想出这样一条生财之路,静心细思,这样坐吃山空,只怕过几天就要沦落街头,但是抛头露面去卖唱,跟平日的玩票消遣又大不相同。左右难以决定,转眼又是数日,屋子里冷如冰窖,她只有一件棉袍,裹着被子还要打哆嗦,茶楼卖唱总好过冻饿而死吧。
端端因为没吃早饭就出门,走在风寒彻骨的大街上,格外觉得冷,两条腿虚软软的几乎迈不动,就想招手叫辆黄包车,低头往口袋里一摸,一个一个查出来,又一个一个放了回去。
到了一壶春茶楼,有伙计领她到掌柜办公的屋子,敲门进去,里面却是两个人,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,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,端端和那青年打个照面,不由惊得退了一步,想不到竟在这里遇到几年前二姨娘介绍给自己认识的刘宏阳,刘宏阳也觉她面熟,但端端此刻的打扮和那时意气风发的林四小姐实在有天渊之别,端详了好一会儿,才认出来,吃惊道:“你不是密斯林——”
端端当初任性,经常戏弄追求的人,这位密斯脱刘就没少吃过她的苦头,一霎间前尘影事兜上心头,真觉百感交集,羞惭之下,转身就向外走,那年纪大的掌柜踏上前笑道:“林小姐,您和我们少东家认识,那就更好说话了。”转脸向刘宏阳道:“少东家,这位林小姐想在咱们这儿清唱一段日子,你看怎么样?”
刘宏阳不住地拿眼睛上下打量端端,哦了一声笑说:“对了,你从前就喜欢票戏的。这样吧,就一月二百块钱,明天开始好不好?”
掌柜脸上露出了诧异的神色,似乎想要说什么,又咽了回去,端端却不知这报酬开得是高是低,只道是通例,她这时为衣食计,也顾不了太多,和二人略谈几句,便回旅馆了。
下午有人送来衣服和鞋子和四十块钱,说是一壶春少东家送给小姐登台穿的,大衣镶着水獭皮领子,里子是花灰鼠,款式比端端送当的那一件还要新。刘宏阳又坐了汽车亲自来接她,端端因为天气太冷,受冻难当,犹豫了一下,还是穿了那件大衣出来,不过叫茶房将其他的东西都搬到刘宏阳的车上,四十块钱也还给了他。
刘宏阳接过钱随手一抛,“这又值什么,反正密斯林是不待见我送的东西就是了。”瞥了端端两眼,微微笑了笑。
端端知他看的是这件大衣,不由脸上一红,牵了下衣襟,“这件大衣的钱能不能在酬劳里面扣。”
刘宏阳微笑,“密斯林和我算得好清楚呀。”见端端不说话,又道:“你看我这辆新买的汽车怎么样?天津卫独一份,这座位能变好几种样子,角落里还装着喷香水的开关,我给你按一下,闻到没有,是玫瑰香味儿。”
若是从前,端端看他这臭显摆的样子,早就要张嘴讥讽,现在也只默默听着,刘宏阳又道:“不如别去茶楼了,让汽车夫开车,我陪你在天津逛两圈好不好。咱们是相识这么久的朋友,朋友有通财之义,我的钱就和你的钱一样,何必这么见外呢。”说话间很自然地就抚上了端端的手。
端端脸色一变,手腕一甩,冷冷道:“我不敢称密斯脱刘的朋友,还是宾主比较好。”
刘宏阳也不生气,收回手,慢悠悠道:“宾主就宾主吧。”
到了茶楼,掌柜迎上来,笑吟吟向端端道:“昨天真是失敬,听我们少东家一讲,才知道林小姐原来是林秘书长的千金。”端端刚想说话,却见几个店伙抬了一块花牌进来,那上面写了八个字,“缙绅后裔,学界名媛。”
端端周身一颤,寒着脸道:“我答应清唱,可没答应拿我家世做什么宣传?刘先生,你这是什么意思?”
刘宏阳笑道:“密斯林,别生气呀。你想想,你又不是唱/红的名角儿,不把身份摆出来,谁要来听你唱呢?我们开茶楼的,总得为营业考虑。况且你不是一向自恃身份高贵,不把做买卖的人看在眼里吗?又喜欢标新立异出风头,我替你宣传一下,让茶座儿都瞻仰瞻仰林四小姐的风采,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?”见端端脸色发青,又低低一笑,“不想唱戏,咱们也有不唱戏的法子,偏偏你又不肯。”
端端看着他嘴唇一张一合,一副惫赖的模样,眉稍眼角尽是嘲笑之意,心道:林端端呀林端端呀,你莫不是傻了吗,这人对你还有好意不成,他是报当日之辱来了。当即啐了一口,“无赖。”转身向门口走去。刘宏阳拍着手冷笑道:“好,有骨气,不过密斯林身上的这件大衣,还是无赖的钞票买的。”
端端只觉全身血都往头上涌,颤抖着把大衣脱了,向身后一抛,挺直身子大步走了出去。出门来被冷风一激,才觉清醒了,她身上只剩一件棉袍,在这寒风凛冽的天气,连骨缝都打冷颤,呛进一口冷风,就扶着墙咳个不停。
路上的人稀稀落落,不是生活所迫,谁也不愿在这种天气出门,几年前在北京这个季节,不是身眠锦帐,就是围炉赏梅,还记得有一次被刘宏阳烦得紧了,答应了赴他的约,不想第二天却忘了,累他在陶然亭白冻一下午,这样看来,他报复自己似乎也没什么不应该。
“梅花,谁买梅花?”一个挑担子卖梅花的老者从巷子经过,担子里露出十几枝梅花,有开得极盛的,也有半含苞的,还记得兰生爬上树替自己折梅花,也是这样红艳夺目,这样想着,鼻端似乎闻到一股幽香,而眼前那抹红色却渐渐模糊起来,端端头重脚轻,再也站不稳,身子晃了几晃,就跌倒在地上。
北风凛冽,卷过几张旧报纸,其中一张上面登了则广告:“冬青旧主慧鉴:忆昔《长生殿》拍曲——但果有精诚不散,终成连理。仆心不改,君岂忘之?冀见报急示居址,勿使人怀想成痴。兰曰。”
虽没有点出姓名,当事人彼此心照。切切念念,仆心不改,桩桩件件,君岂忘之?——自春徂秋,他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她。
可惜文字无知,不知道要找的那个人就在眼前,报纸褶皱地翻卷着,一阵风刮起,它便荡悠悠地从她身上飘过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