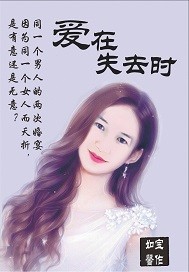林家旧宅,端阳坐在沙发上,将信封向端端方向一推,劝道:“你生病那会儿,云鹏因为剿匪的事脱不开身,还特意写信向父亲解释。带兵打仗,哪是自己说话算的,你就不要再记恨他了。这既不接电话,也不看信,到底还要僵多久呢?逼得人家没办法,只好托我转递,你还是快点儿拆开看看吧。再不拆,我就替你拆了。”
端端目光扫过信封上“端端爱妻亲启”几个字,不由嗤笑了一声,抬头向端阳道:“三哥,你别劝我,我是一定要和他离婚的,至于这封信上写什么,不看也罢。”
端阳叹口气,“你呀……”索性拿起信封,撕开了念给她听:
“端端,知道你病已痊愈,我总算放下心里一块大石。一直没能陪在你病床前,你怨恨也是应该的,但离婚一事,我绝不能答应。自你走后,我常常回想起我们在一起的幸福快乐日子。既然能做夫妻,总是上辈子的缘分,我有很多话要和你说,现在剿匪的事情结束了,等司令部的会议开完,就到北京找你。你负罪的云鹏上”
这封信写得深情款款,不怕拿给任何人看。怪不得林家人都觉得,小夫妻吵架是常事,端端动不动就提离婚,未免太小题大做了。端阳甚至还试探着问她,是不是和家桢还有联系。
如果端阳不说,端端都不知道家桢曾在国外给她写过信,没有收到信的原因,不论是意外还是人为,时至今日,也没有追究的必要了。现在的她,早失去了当初的热情和勇气。何况就算出国,她绝不肯顶着尚太太的名头出去,那样无论走到天涯海角,都觉得身上打了一个羞耻的烙印。
她和尚云鹏的种种,即使亲近如端阳,也无法启齿,更兼回到北京以后,根本不愿意回想从前的事,每一思及,忙强迫自己转开念头。
端端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极满,下午去公园电影院消遣几个钟头,吃过晚饭,去戏院看戏,十一二点的时候再去饭店跳舞,半夜才回家,睡到第二天下午两三点钟,起床去公园,周而复始,就这样一天一天消磨过去。
可是眼下这一刻,强迫自己转开念头的办法已经行不通,记得林绍钧三周年祭的时候,她要回京祭扫,那时候尚云鹏正得李督重用,怎肯轻易离开,看她一眼,拧着眉头说:“我这当口怎么走得开,你在哪里烧纸不是烧?”
端端双手紧攥着衣襟,“那我自己一个人回去。”
尚云鹏微微冷笑:“你一个人回去?现在去欧洲的行线通了,你如果坐船跑到法国找徐家桢,我去巴黎捉你回来不成?”
端端气得直掉眼泪,“你又发什么神经。”
“怎么,戳到你的痛处了?”尚云鹏斜睨着她,“结婚这么久,你在我面前笑过几次,想当初和徐家桢在一处的时候,又腻成什么模样,我在旁边看着都跟着肉麻。”
端端恨恨道:“那你还跟我求婚?”
尚云鹏淡淡一笑:“林秘书长的千金小姐,北京城最美丽的一道风景,带出去谁不羡慕?你看我待你多好,就算你一天到晚死气活样的,我也没像你爸爸那样往家里领小老婆。那些下等女人算什么,只有像你这样标标致致的名门小姐,才配站在我尚某人的身边。”
端端呸一声,起身往外走。
尚云鹏抓住她的胳膊往回一扯,“我说过让你走了吗?”端端给他拽了个趔趄,急忙扶住门框站稳,慢慢抬头,嘴角泛出一丝笑意:“好一个有心胸、有见识的新式军人,开赌、庇娼、运鸦片,外表看着像个人,放在锅里煮一煮,跟秦福奇是一个味儿。和你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,我就是想忘徐家桢也忘不了——”
一句未了,尚云鹏已经一巴掌扇过来,端端被打得整个头歪到一边,双耳嗡嗡作响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尚云鹏冷冷道:“你在丈夫面前念着别的男人,我不该打你么?”
四周一下子静下来,只剩下白炽灯发出的咝咝声,端端委顿在地毯上,身体止不住籁籁发抖,哆嗦着说不出话。
尚云鹏看了她一会儿,又上前张臂抱住她,抬手抚着她的脸颊叹息:“宝贝儿,不要整天和我怄气,惹恼了我,于你又有什么好处呢?”他俯下身吻她,贴在她耳边说:“我为娶你花了多少心思,你为什么对我总是冷冰冰的,姓徐的不过是个没权没势的穷书生,哪里比得上我?只要你肯对我温柔一点儿,我怎么舍得动你一个手指头……”
沿着的颈项不住吻下去,气息慢慢包拢,端端只觉全身寒毛孔都翻起来,阳光掠在窗纸上,光线一点一点移动,她几乎能听到血液在自己血管里哗哗的流淌声。
当初只为逃避秦福奇的纠缠,匆忙和尚云鹏结婚,想不到竟是前门驱狼,后门进虎,可惜她明白得太迟了
后来偷偷托人买了火车票,结果还是被发现,尚云鹏看管得越发紧了,每天四五个护兵守着,简直连大门都出不去。有一天睡到半夜惊醒,听见外面淅淅沥沥的声音,想起刚来这里的那一天也是这样的雨,这三年也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,将来还有多少日子要熬,思及老父,只觉悲从中来,不由哀哀地哭出声,恍恍惚惚地站起来,走到雨幕中,倾盆的大雨淋在身上,一遍又一遍,却怎么也洗不尽满身的羞辱。
尚云鹏一早醒来,听到外面有人唱歌,叫马弁出去看,回来结结巴巴地禀报说是太太,忙穿了衣服出来,只见端端全身湿淋淋的,双目茫然,痴痴站在泥水地里。他走过去扯了她一把,喝道:“你不要命了!”
端端的腿早已站得麻木了,一扯之下立刻摔倒,整个人就摔在泥地里。晚上发起烧来,迷迷糊糊地嚷:爸爸,你怎么不来带我走!请来大夫用药,一直也不见大好,只两三个月光景,人就瘦得不成模样,有一天半梦半醒间听到尚云鹏恶狠狠喊:“行,我成全你,送你回北京,你千万不要给我死在路上。”
病得这样重,他大概以为她会死掉,她也以为自己会死掉,可是拼拼挣挣,竟然又活了过来。在西山休养了几个月,还是三年前的风头无两的林四小姐。
现在尚云鹏又要来了,他说,只有像你这样标标致致的名门小姐,才配站在我尚某人的身边。名门小姐,文明太太——这是尚太太的资格,他不肯放过她,也不肯放过他自己。